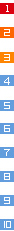今年以來,有十多個省、市相繼宣布上調最低工資標準,但大多數已經上調最低工資線的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仍不足千元。深圳的最低工資標準以前為每月900元,現在為1100元。北京以前的最低工資標準為每月800元,現在也才960元。
一次性漲薪百分之二三十,應該算大幅提升了。但新的工資水平仍然不能令人滿意。一方面,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標準,往往成為企業的最高標準,員工想多掙錢,必須加班加點地工作,從深圳到北京,情況似乎普遍如此;另一方面,此前的工資水平太低,漲幅再大,漲薪后的工資額并不高。馬克思曾評說:“所以不應當陶醉于動聽的工資水平提高的百分比。必須經常這樣問:原來的工資數是多少?”馬克思之問具有現實意義,漲薪之后仍徘徊于千元左右的工資水平,使得打工者在如何于城市安身立命這一設問面前顯得非常尷尬。
“基本生活水平”要贍養打工者及其家人
當前在中國城市生活,最低工資該是多少?由于不同城市的生活水平差距較大,一個統一的最低工資標準并不存在,但世界銀行調查報告的以下數字可供我們參考。考慮每人每天的營養攝入量及養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國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平均費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在上海、北京、深圳這樣的大城市里,1600多元的工資大體上仍屬于“活命”的水平。不過,在世界銀行的“活命”標準里,其內涵已經較為豐富了,這個“基本生活水平”不是給打工者個人定的,而是為打工者及其家人所定。但現在各地新出臺的最低工資標準并沒有把員工為繁衍后代所需的費用計算在內,即只計算夠一個人而非一家人活命所需要的工資額。
經濟學家對最低工資存在共識
最低工資標準必須把工人維持自身的生存和繁衍后代所需的成本計算在內,這不只是現代社會才應當采用的計算方式,而是為歐洲自工業化以來所沿用。馬克思、恩格斯,以及歐洲工業化以前和工業化時期的其他思想家、經濟學家對此都有共識,他們都認為,工資額一般應保證工人維持生活和有可能延續后代。
熊彼特說,亞當·斯密是對工資理論進行系統闡述的第一人。斯密認為,“需要靠勞動過活的人,其工資至少須足夠維持其生活。在大多數場合,工資還得稍稍超過足夠維持生活的程度,否則勞動者就不能贍養家室而傳宗接代了。”斯密得出結論:“為贍養家屬,即使最低級普通勞動者夫婦二人勞動所得,也必須能稍稍超過維持他倆自身生活所需的費用”,這樣的“工資是符合一般人道標準的最低工資”。
盡管斯密把養育后代的需要計算在最低工資里,但他并沒有提供充分的理論解釋。而馬克思的工資理論對雇傭勞動制度下的最低工資作了最深刻和最具有穿透力的論述。
馬克思認為,在雇傭勞動制度下,勞動力是一種商品。工資則是勞動力價格的特種名稱。工資與其他一切商品的價格一樣,由市場規律決定。首先是供求關系。“勞動報酬忽而提高,忽而降低,是依供求關系為轉移的,依購買勞動(力)的資本家和出賣勞動(力)的工人之間的競爭情形為轉移的。”其次是商品的生產費用。在上述波動的范圍內,勞動力的價格是由再生產勞動力商品需要的費用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決定的。勞動力本身的生產費用包括為了使工人保持其為工人或把他訓練成為工人所需要的費用。因此,某一種勞動所需要的訓練時間愈少,工人的生產費用也就愈少,他的勞動力價格即他的工資也就愈低。工人勞動力的價格由必需生活資料的價格決定。馬克思特別指出,即使在簡單勞動的生產費用中也要加入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工人的損耗也和機器的損耗一樣,是要計算進去的。總之,簡單勞動的生產費用就是維持工人生存和延續工人后代的費用。這種費用的價格就是勞動力的價格。這樣決定的工資就叫做最低工資。
有意思的是,從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有關論述中,我們發現,那些受到馬恩批判的人對于最低工資的看法也是如此。比如在《反杜林論》中,恩格斯說,“不管杜林先生怎樣多余地把工資改稱為報酬,他也還是認為,它一般地必須保證工人維持生活和有可能延續后代”。拉薩爾的“鐵的工資規律”是一個著名的、但受到馬克思嚴厲批判的論斷。拉薩爾認為:“這個在現今的關系之下,在勞動的供求的支配之下,決定著工資的鐵的經濟規律是這樣的:平均工資始終停留在一國人民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習慣所要求的必要的生活水平之上。”在這里,平均工資就是最低工資,它要包括“為維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所必要的費用。
由上述可見,最低工資不應只是為勞動者個人生活所需的最低報酬,而是至少足以養家糊口的報酬。
最低工資與勞動力實際價值間存在價差
雖然最低工資至少足以養家糊口,但這并不意味著工人只能掙到夠一家人活命的工資。
馬克思曾指出,這種最低工資不是就單個人來說的,而是就整個種屬而言的。就特定的地區、國家、社會和文化環境中的工人或工人隊伍而言,他們的工資并非必然要被限定在維持生理需要的水平上。
根據《資本論》,工資的最低限度是由工人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力時在生理上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規定的,但是,勞動力的實際價值和這個生理最低限度是不一致的。國家、地區之間的氣候和社會發展水平不同,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也就不同,所謂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圍,和滿足這些需要的方式一樣,本身是歷史的產物,因此多半取決于一個國家的社會文化水平,其中主要取決于無產階級是在什么條件下形成的,有哪些習慣和生活要求,其組織程度和反抗資本斗爭的發展。工人為了獲得某種勞動技能和技巧,需要有一定的教育和訓練,這也必須包括在生產勞動力所耗費的價值總和中。因此,與其他商品不同,勞動力的價值規定包含著一個歷史的和道德的因素。
從馬克思的論述中,我們不難發現,滿足最起碼生理需要的最低工資,與由于社會和文化發展水平的不同而形成的勞動力的實際價值之間,存在著一個價值差。工資是勞動力價值的價格,工資的上下波動,既是價格圍繞價值的波動,從長期看,又反映了價值差的縮小或擴大。從歷史上看,正是為了爭奪這個價值差和價格差,勞資雙方發生過長期的、激烈的斗爭。
斯密早就發現,勞資雙方的利害關系絕不一致。勞動者盼望多得,而雇主希望少給。勞動者都想為提高工資而結合,雇主卻想為減低工資而聯合。起初,工人缺少組織,而工廠主因為人數少而容易結盟,形勢對工人不利。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中所引用的史料,揭示出19世紀初的工廠主之間有一種討厭的聯合,還規定:任何工廠主必須查明,如果工人是被他原來的主人解雇的,便不能再雇傭。在這種情況下,工人不得不服從老板。
為了對抗雇主、爭取自己的利益,工人也開始聯合起來。歷史表明,只有通過有組織的工人反抗,才有能力爭取到上述差價中的上限。
現今中國相當多的非公有制企業中的打工者為了掙到超出于起碼的生理需要的收入,往往要加班加點。比如在富士康,打工者“每周從事80個小時左右的簡單機械性工作”。5月28日,北京現代零部件企業“星宇車”公司也發生了員工停工事件,抗議工資低、勞動強度大。據報道,由于當時該企業員工的基本工資僅為北京市的最低工資標準,所以,加班對于每名員工都很重要。富士康公司和現代“星宇車”公司都是外資企業坐落在大都市中代表先進生產力的企業,其工人階級的狀況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別的企業了。
探討了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思想家、經濟學家的有關論述,我們對于在大多數非公有制企業中勞動者所處的艱苦勞動環境和低下收入,也就不難作出理論的解釋。歐美工業化的歷史表明,“如果不對資本加以限制,它就會不顧一切和毫不留情地力求把整個工人階級弄到這種極端退化的境地。”最能夠對資本加以限制的力量當然是政府。馬克思說過,無論在英國或其他各國,對工作日的限制“從來都是依靠立法上的干涉”,但“這種干涉如果沒有工人方面的經常壓力,是永遠也不會出現的”。 | 




b2dca2d2-a3b3-4d89-bd82-c00566ddbffb.jpg)
fa44e9bd-5f72-4363-9d51-31e10a5cad99.jpg)
41cd398f-3067-4c06-9aff-50b33a2b54bc.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