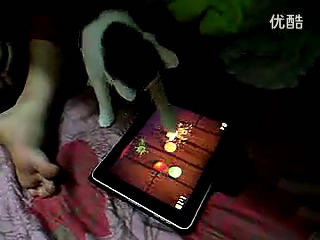自相矛盾的自決政策
自決是20世紀后期美國印第安人政策最突出的特征。所謂自決,是指美國政府承認印第安人社會與美國主流社會在文化上存在差異,而印第安人無需改變這種差異,印第安人可以行使自決權繼續生活在保留地上,具有治理自己事務和經濟事業的權利。
1934年美國國會通過了“印第安人重新組織法”,該法旨在修正“道斯法案”,消除強制同化印第安人所造成的后果,肯定保留地繼續存在的重要性。該法案實施后,印第安事務發生了質的變化,保留地內的土地分配終止了,印第安部落體制得以復興,許多部落不同程度地進行了獨立的領導工作。但1953年開始實施的終止政策卻再次將廢除保留地、解散印第安人部落作為聯邦政府的印第安人政策目標。這一政策激起了印第安人的強烈反對。在民權運動和多元文化的大背景下,1968年3月6日,林登·約翰遜總統在一份題名為“被遺忘的美國人”的致國會特別咨文中,明確提出結束終止政策,要求政府幫助印第安人,并將印第安人自決作為政府印第安人政策的新目標。根據印第安人自決這一主導精神,1968年通過的“印第安人民權法”擴大了保留地內印第安人的權利,承認基于印第安人文化傳統而擬就的各部落法律的存在。截至20世紀末,歷屆美國總統在任內都一再公開承諾印第安人自決,重申將“按政府與政府間的原則處理與印第安部落間的關系,并繼續實行印第安部落自治的原則”,明確表明“印第安人能夠成為聯邦管轄之下獨立自主的人,而不會失去聯邦的關心與資助”。在自決政策下,印第安人的政治和文化權利得到了越來越多的承認和保護。今天,美國聯邦政府承認的印第安人部落已有564個,這些部落組織管理自己的保留地,行使政府職能,包括對部落成員行使刑事和民事訴訟的職能。部落政府在印第安人事務中發揮著積極作用。
表面上看,部落政府的自我管理職能似乎意味著組織完善、管理有效的印第安人部落得到了與聯邦政府等同的對待。但部落自決是由美國政府自上而下授予的。事實上,印第安人事務的最終決定權仍掌握在聯邦政府手中。這造成了一種矛盾現象:一方面印第安人要求部落自主與自治,另一方面,印第安人又不得不要求聯邦政府繼續其對印第安人及其資源的托管職責。但政府托管職責的持續存在帶來的必然后果是家長制統治的繼續存在,托管職責的擴大也必然導致家長制統治的擴大。部落自決有賴于強有力的部落自治與保留地內印第安人經濟的自給,但從目前情況看,印第安人無法做到這些,長期以來印第安人經濟嚴重依賴聯邦資助,印第安部落實質上不具備自治政府的真正含義。主流社會與印第安人之間仍存在著沖突。
迄今為止,奧巴馬政府并未明確印第安人政策的走向,但在2008年總統競選期間,奧巴馬曾明確表示支持印第安人自決。然而,印第安人卻并不樂觀,無論是生活在城市底層的印第安人,還是在保留地仰賴政府資金投入的印第安人都面臨著美國主流文化的強大沖擊。一個世紀美國印第安人政策的演變告訴他們,即使不是現在,至少在將來某個時候,鐘擺會再次從自決擺向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