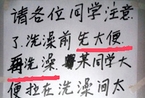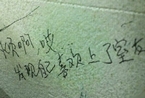養老金并非延遲退休的基本依據
www.hxt111.com?2013-05-09 15:37? ?來源:光明網 我來說兩句
|
記者:說完歷史上的養老金缺口,我們再談談養老保險金的現狀。 鄭功成:當前養老保險的財務狀況總體良好,有三組數字支撐:一是國家審計署2012年對全國社保財務的審計報告,2011年全國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收入15603.58億元,比2005年增長243.51%;支出11425.64億元,比2005年增長224.05%;2011年底該基金累計結余18500.41億元,比2005年底增長413.40%。二是人社部公布的2012年全國職工養老保險基金收支狀況,當年總收入19693億元,總支出15502億元,結余4191億元,累計結余達23667億元。三是財政部在2013年“兩會”期間向全國人大提交的社會保險預算報告,2013年全國社會保險基金預算收入3.28萬億元,預算支出2.79萬億元,結余4915億元,年末滾存結余40943億元,其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構成這一巨額結余的主體部分。上述數據已清晰地反映了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財務狀況良好。我不理解為什么媒體與公眾不關注這些信息,卻偏偏對所謂的養老金缺口如此感興趣。有人說這種結余中有財政補貼部分應當扣除,這是不懂社會保險制度常識所引起的,因為這一制度在德國產生以來就是由政府分擔責任的,何況我國的財政補貼事實上還只是對計劃經濟時代必須負責到底的中老年職工的歷史欠賬的一種補償。 記者:未來養老金預期是怎樣的? 鄭功成:我在2007年主持“中國社會保障改革與發展戰略”項目研究時,曾組織過相應的測算,在綜合考慮多種影響因素的條件下,我們在當時得出的基本結論是2030年前是基金持續結余的時期,而到2030年后則會出現年度缺口,但前期的結余足以再支撐10年以上的收支平衡,再往后則需要動用戰略儲備基金,但并不存在巨大風險。一方面,伴隨人口老齡化的加速發展,退休人員會持續增加,養老金的支付規模也會持續擴大,在所有條件不變的情形下,最終當然會出現收不抵支甚至缺口越來越大的局面。另一方面,影響養老金收支的因素也必然會發生重大變化。例如,在未來數十年間,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必定持續提高,財政收入會持續增長,養老保險費伴隨工資增長也必然會持續增長,退休年齡到2030年可能會發生變化,再加上已經建立的社會保障戰略儲備基金與不斷做實的個人賬戶,以及龐大的國有資產與土地收益可以作為養老保險制度的重要物質基礎,這些都是有利于維護養老保險基金收支長期平衡的因素。因此,所謂的未來幾十年后會出現巨大缺口的說法,其實只是未考慮上述因素變化的計算結果。類似的計算在其他國家也會出現,它可以提醒政府對這一制度保持理性,但不會影響公眾的信心。 養老金并非延遲退休的基本依據 記者:延遲退休和養老金缺口有無關系,為什么? 鄭功成:我一直不贊同將減少養老金支出作為延遲退休年齡的基本依據,因為退休年齡的延長與否主要應取決于人均預期壽命、受教育年限及人口結構與就業狀況等要素,如果人均預期壽命延長、受教育年限延長、人口結構老化、就業需求擴張,則必然要延遲退休年齡,反之亦然,而減少養老金支出只不過是在追求上述目標的同時產生的一個客觀結果而已。因此,我認為在決定我國是否延遲退休年齡時切不可本末倒置。在國際上,最有發言權的無疑是第一個建立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的德國,該國采取現收現付財務模式,養老賬戶資金始終充足,2011年還盈余45億歐元,德國政府決定從2012年將養老保險費率從19.9%(勞資繳費各占50%)降至19.6%,并宣布2012年養老金待遇繼續提高,但同時也從2012年1月1日開始延遲退休年齡,即從現行的65歲逐步延長到2029年的67歲。世界養老保險制度的創始國并非因養老金缺口而延遲退休年齡,而是以人均預期壽命延長與人口結構變化作為依據,這是維護代際公平的需要。況且,我國的養老保險基金并不存在缺口問題。一些地區出現年度收不抵支現象,不過是這一制度處于地方分割狀態下的畸形結果,它不能掩蓋全國養老保險基金累計結余持續增長的客觀事實。因此,以局部地區養老金缺口為由來解釋延遲退休年齡顯然是說不通的。 記者:對待養老金問題,國家做了哪些政策準備?還需要做哪些準備呢? 鄭功成:2000年建立的全國社會保障基金是一種有遠見的戰略儲備,它現有規模近萬億元,如果再加上不斷做實的個人賬戶基金,積累的基金總量會持續壯大。今后需要進行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盡快實現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這是徹底解決部分地區收支缺口問題的治本之計;二是在集中管理、確保安全的條件下,對結余基金采取合理組合的方式進行有償運營,真正實現保值增值的目標;三是厘清歷史欠賬,并用歷史的方法化解這種債務,讓新型制度輕裝上陣;四是調整責任分擔機制,包括明確政府的責任及其承擔方式,均衡用人單位與參保人的繳費負擔等;五是有序推動補充養老保險發展,真正構建多層性的養老保險制度。總之,政府要以理性來優化制度安排,學者要負起科學研究與理性發聲的責任,公眾對這一制度則應當具有足夠的信心。(記者 柳 霞) |
- 心情版
- 請選擇您看到這篇新聞時的心情
- 查看心情排行>>